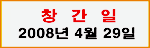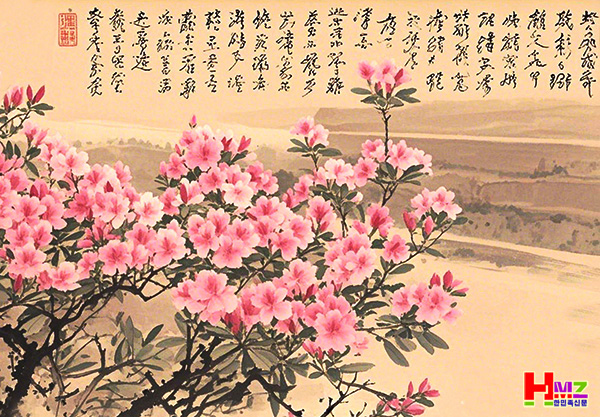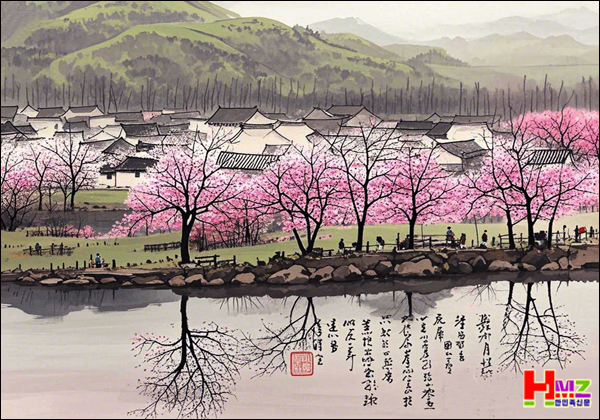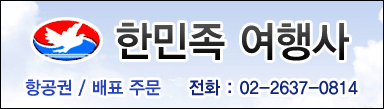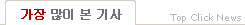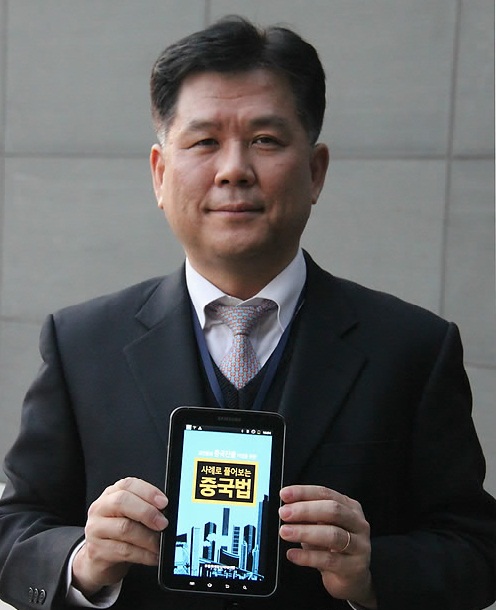图为刘筱石对话王智远
王智远,1984年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89年去澳大利亚留学并在悉尼美术学院完成了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被广泛认可并且参加了许多国内外的重要展览,作品被收藏于澳大利亚国立艺术馆、昆士兰当代艺术馆以及悉尼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和国际其它的收藏机构。
在澳大利亚生活11年以后,他于2002年回到中国,目前作为独立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北京。自2006-12年他作为收藏顾问与收藏家朱迪女士共同创建了澳大利亚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并参与了所有鉴别与收藏作品的工作,如今位于悉尼的白兔收藏已经是世界最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之一。
刘筱石,策展人、艺术评论者,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展览策划、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论研究与写作,2013年至今,任上舍空间艺术总监。
刘筱石(以下简称刘):上舍空间三月八日刚刚开幕的展览是由三个厅同步开展,其中C厅是一个实验展厅,这也是实验展厅的第一回展览,这个展览是由艺术家王智远来完成的。其实这个展厅最初是一个仓库,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厅开放利用起来,另外从艺术发展本身来说,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突破壁垒、重建秩序是必然,所以C厅的开设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性质的展厅来激发更多的可能。那我之前对你的作品有了解,包括从早期的《一生二》,还有后来的《内裤》作品系列,《龙卷风》等一些装置。我觉得在这个期间,你对自身语言延续的基础上是又做了一些突破性的尝试,去年我看到你的一件叫做《取暖》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作品很有意思,就这件作品本身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C厅,这是当初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春节前邀请你来展示这件作品,当时我们最初谈论关于《取暖》这件作品在C厅实施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王智远(以下简称王):春节前从你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新的画廊在筹划,要做一个新的展览,但是怎么新,什么样的新我完全不知道。当时提出来邀请我展示《取暖》这件作品,按辈分来算我应该是你们老师那一辈了,但是我喜欢接触年轻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因为我害怕我自己的观念老了,所以被邀请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对于这件事情没谱。因为之前在富思画廊展示的时候画廊为此作品的实施提供了非常好的墙面,对新画廊的空间我不知道什么样子,不过我自己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取暖》作品使用的材料有一个功能就是特别能适应环境,根据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制造不同的效果。所以当时我没有想的太多,也没有为即将来临的展览做什么准备,直到展览开始之前的十天才看到展示空间。
刘:最终展示的作品是《侵食》,这个作品的实施应该还是春节回来后我们去看完空间,然后重新做的决定。
王:对,当第一个展览彻底结束后,准备第二个展览的时候,才把房间打开给我看,当时里面还是个仓库,当腾出空间以后我才发现正对着门的那面墙的面积是不够做《取暖》作品。因为《取暖》需要一个适当的面积空间来扩张,而这个空间迎面的墙是3.2米宽,而纵身很长,不适合制作《取暖》,必须构思其它的方案来代替,其实我挺绝望的,因为离展览开幕只有几天时间,对于新作品我是没底的。《取暖》作品的组成--一根电线和一个灯泡,用文字组成的像苍蝇一样的围绕着灯泡产生密集的效果。但如果把"苍蝇"转换成其他的一种效果是不是能继续有意思,我因为没做过,所以完全没有经验。当时看完以后我就赶紧回去设想,构思,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因为心里有事儿转天的凌晨3点多就睡不着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无意中想了"地图"是否能够放在这个空间?我立刻起来开始画。直到6点,我画了四张草图,早晨起来我就给筱石打电话,过来一起看我的构想,看看针对这个空间哪个比较有意思,最后我们共同觉得"地图"的设想最有意思,就这样定下来了。
刘:对,过程是这样,刚才你有提到灵感与理性创作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理性创作是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为所谓的灵感是即时、虚幻的,后续的理性推敲过程会显得比较重要一些。
王:我觉得灵感就好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它来源于平时的思考。比如说,去年(2013年)的7月份完成的《取暖》作品并展览,后来的这么长时间我什么作品都没有做,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取暖》这件作品,作品表达了什么?为什么?与我之前的作品有什么区别,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是什么等。有一点我应该说,谢谢筱石在这件作品里面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推动作用。因为,作为一个策展人跟艺术家之间这样开放式的一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作为创作者,会有很多创作想法的选择,有无限的可能,策展人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重要了,因为作品也是与整体的展览布局有关系。策展人、批评家和艺术家能够产生互动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都在面向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艺术将会怎么样?什么是我们希望的?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就会产生有意思的东西。最后画廊给我请了三位年轻的艺术家和画廊的几位员工一起,加上我本人共同参与花了五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件作品,最后这件新作品的题目叫《侵食》。
刘:《侵食》和《取暖》两件作品关联性很大,《取暖》这件作品是有积极的和消极的词汇组成,你想呈现一种苍蝇密布在墙上的感觉,因为昆虫具有趋光性,会密布在灯泡周围,同时词条和苍蝇是一体的,这时苍蝇所携带的属性是有意思的。那关于《侵食》这件作品,在材料上是与《取暖》一致的,这是你个人语言的强化还是一个系列推进?
王:作品《取暖》使用的是两个中文文字的词组,贴在墙上远看像是苍蝇围绕着灯泡,是往里(灯光)聚的形式,而《侵食》刚好相反,是往外散的形式。我很希望作品《侵食》最后的效果不只是一面世界地图,是"苍蝇"们在解体这个地图的过程,因此,在似是而非中找到"地图"在流动的感觉。我在完成《取暖》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作品《侵食》的产生,就如同我还不知道使用这个"帖字"的材料还能出现什么作品一样,因此我不敢说产生一个系列。我想表达的是,我会继续拓展"贴字"材料的可能性,但任何的媒介都有它的极限,我不会死磕在一个媒介里。
侵食综合材料2014 王智远
取暖综合材料2013 王智远
刘:我觉得这种呈现方式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就这两件作品的材料来说没有明确的属性和指向性,但是你以前的《龙卷风》之类的作品,像垃圾瓶子这些材料的指向性很明显,蕴含着一些属性,还有更前面的《内裤》作品,用木雕做出丝绸的质感,这存在着一些反差,所以当材料被弱化或本身处于"无属性"的时候,可能性会更大。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之前的装置作品都是可移动的,而这两件作品是不可移动的。
王:现在回头看以前的作品,尽管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他们的相通点是可移动的、可触摸的。而这两件作品是不可触摸,不可移动的,而且随着展览结束它也就消失了。新的作品与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同时也更不像所谓的作品。
刘:适应环境这个问题在你之前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像《一生二》等作品,根据环境有一些不同的放置。这会不会是你作品形成的一种语言?
王:2000年的一套作品,叫做《碎片》,是由40件碎片组成,这件作品是我的研究生的毕业创作。这件作品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方式,40件图像都是抄袭别人的。我当时受到里奇特斯坦的影响,他是生活在别人的想象里--不用自己想象力,他的作品来源于其他人的作品。就好像小虫子依附在人的身体上,吸食别人的血液存活。我的40件作品,我也都是抄袭别人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茶杯,杯上的图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在复印机里进行复印,或者在包装盒或者书上看到有意思的图像,把它们收集来,然后放大到我需要的程度。悉尼美术学院有个非常棒的工作室,非常大,像仓库一样。里面非常现代化,有各种处理金属和木头材料的工具,还有一个指导老师,我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因为我的作品观念,作品展览摆放的时候我也没有参与,当时那里有三个工人,我拜托他们给我摆作品,我自己出去遛弯了。等我回来以后,我一看,哇!真不错。所以那个作品我不但放弃了想象力,而且也放弃了作品的含义。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主要论述的是--作品、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生活的环境这三者之间的流动性是什么?总结我2000年的作品和论文给我的最大收获是:我寻找到了一种表达艺术的方式,这个方式能够适应我不断变化的生活。其实艺术家不只是创造了艺术品,艺术品往往又反过来制约和要求着艺术家,艺术家与其创造作品的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回顾2000年完成的《碎片》作品,明显的与这件帖子作品《侵食》有内在联系,就是作品的流动性和适应性。
刘:那么这是不是你创作中的个人语言?
王:其实我们学艺术的,受到的教育给了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成功的艺术家都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比如达·芬奇、伦勃朗和梵高都一样,还有安迪·沃霍,这些大师都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语言。这个想法放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今天的信息量太大了,而且我们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所以我对我自己完全是放开的,不固定的,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内在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相同的,但是我是完全不想在作品样式上固定一个什么"自己的独特风格"。
刘:我知道你早些年是在中央美院,后来去的澳大利亚,之间又游历了不少地方,这个经历会不会跟你作品的跨度比较大有关系?
王:太有关系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做自己专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是希望做些新东西,在艺术上叫突破。能不能突破和突破多少不只是胆量多大,还在于你的知识面有多大,你知识的跨度多少,决定了能把它折腾到多少。也可能有些人善于利用这些,有些人不善于,除此之外,突破和创新都在于你的知识。比方说我,性情中就有些求新求好玩的部分,这是肯定的,又加上在央美呆了十年。这十年给了我一个好的影响是,因为如此多优秀的人聚在一起,给了我广泛接触的机会,这些艺术家的起起伏伏,成功和失败都看在眼里。从学院走出来以后去了澳大利亚,等于离开了象牙塔把自己放逐了出去,在日光下暴晒了十年,所经历的与学院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些都会给我种下了不同的基因,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作品都产生很大影响。
刘:个人经验对艺术家的创作影响会很大,但这其实又是依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比如说从19世纪末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上半叶这半个世纪的艺术潮流此起彼伏,因为工业革命对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改观,这会影响到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当然其他原因也是有的。
王:20世纪是视觉艺术探索观念和形式的世纪,几乎无所不包。这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提出更加难以应对的挑战,首先是你为什么要弄艺术?必须找到自己制作作品的原因。如同过去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黑屋子里,不自由很难受,一天屋子的窗子和门都打开了,屋子亮了,我们自由的奔了出去,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者沙漠,没有任何的标记,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到那个方向走?这是一个简单但可以要命的问题,能够抬腿跨出的一步的前提就是找出做这个决定的理由。今天每个艺术家制作作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刘:所以说,当代艺术对于既定模式的突破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像日本的批评家千叶成夫的著作《日本美术尚未形成》,前几天简单聊过,日本和中国有一些相似,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西方语境下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接下来要走的是要突破西方语境后,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或者是结合自身本身传统的系统。
王:这本书我大体看完了,通过千叶先生的论述对于"物派"以及"后物派"有了了解,尤其是论述草间弥生和川保正部分对于我有帮助,当然有些方面我可能有请教的地方,但应该肯定的是千叶先生苦心积虑的寻找日本人作品的精神。其实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现代艺术也好,当代艺术也好,基本是受西方艺术影响,不管是思考方式,艺术语言,批评方式,并且接受了当代艺术这样的一种"国际语言"的表达方式。我认为,随着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强势话语的传播,在世界不同的文化范围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其一是:接受这一"国际语言"并结合本地区的文化整合出他国人可以理解的本国当代艺术。其二是:每个民族都有本土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国画、剪纸、陶瓷和家具,还有非洲的雕塑、日本人的日本画、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点"画等都会继续保留本民族的习惯继续各自的发展。这两种方式之间是相互交流、吸收,同时也是互不相容并行的。我对于"突破西方语境"基本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你根本找不出"你"和"他"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没有界限又何为突破呢?
刘:我觉得界限是有的,只是我们把自己置于了他者的语境下,所以模糊了界限。前段时间在美国大都会有一个水墨展,那个展览本身我们不做讨论,问题在于国内众多艺术家的反应,认为这是一个水墨机会、是西方对国内艺术的重视,包括之前的集体威尼斯之旅,其实这反映了标签的重要性、自身的不自信,同时我们还是一直站在西方艺术体系里在谈问题。
王:这些现象更加凸显了一个问题:经过30年的引进和创新,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该有的都有过了。如果说在早期的时候,西洋人通过各种收藏和展览,有意无意的鼓励和支撑了(也可以说塑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该学的都学到了,西方该有的也都有过,这时候恰恰需要我们自己去确定自己--我们能够是什么?到这个时候你的那泡尿别人是闻不出来你的特色是什么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泡尿应该骚在哪儿。但目前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这需要一个整体,个人微不足道。














 Powered by Newsbuilder
Powered by Newsbuilder